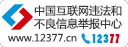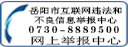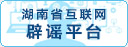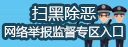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 戴金波
秋高氣爽的周末,我本想到長江邊的大磯頭去看看秋日長江水落石出的模樣,并實地感受一下昔日陸城八景之“楊林晚渡”的繁華。想不到,竟然有意外的驚喜。
深秋的大磯頭,磯高水低,巉崖壁立,高大的石磯和纖夫棧道全部裸露在長江邊。我一個人在大磯頭的頂層花崗巖平臺上踽踽獨行,走到棧道的盡頭視野豁然開朗,西邊幾百米處的一個小山頭引起了我的注意。銅鼓山?那肯定就是小嘰頭銅鼓山了!突然之間,我好像打了雞血一般,猛然來了精神。聽說銅鼓山有商代文化遺址,近在咫尺的歷史文化遺存,為什么不去看看?一下子我的關(guān)注點就由大磯頭轉(zhuǎn)到了神秘的銅鼓山。因為,銅鼓山上有太多的秘密。
銅鼓山其實離我老家并不太遠,大約3公里的路程。兒時只知西有馬鞍山,不知這方臨江丘陵暗藏商代文明。相傳山頂曾有銅鼓自鳴,如今更因2013年被列入全國文保單位而聞名,但由于少小離家、長期在外工作,我還從未拜訪過。
銅鼓山說是山,其實也就是一個小山丘,海拔只有47米,靠長江的一面是一個圓弧形的磯頭,當(dāng)?shù)厝朔Q之為小嘰頭。另外三面都是長江千萬年沖刷形成的沖積平原。正因為四周平坦開闊,小小的銅鼓山看著還像座山。
銅鼓山上有商代文化的遺址,整個遺址面積達5.8萬平方米。據(jù)專家考證,這里的商代文明一直延續(xù)到了東周時期,前后有近400年歷史。然后好像一夜之間又突然消失,連同商周人的生活痕跡也一起被深深埋藏起來。3000多年之后,銅鼓山掩埋的驚天秘密,才逐步被當(dāng)代人知曉。據(jù)《湖南考古輯刊》(第五集)披露,198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對該遺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發(fā)掘,發(fā)掘面積400多平方米,并發(fā)掘清理了東周墓葬7座。商代遺存出土的陶器有鬲、大口尊、簋、爵、斝、盆、南瓦、大口缸、罐、鼎、釜等,石器有錛、刀等,銅器有箭鏃、泡、削等。東周墓出土有鬲、盂、罐、鼎、敦、壺、盤、匜、匕、勺、銅劍、銅矛等。其中1997年出土的青銅鼎為國家一級文物,青銅觚為國家二級文物。銅鼓山的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打破了史學(xué)界長期以來形成的“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使該遺址成為了長江以南極少保存有中原商文化的遺址之一,對于研究商文化南下及其與當(dāng)?shù)赝林幕年P(guān)系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銅鼓山商代文化遺址的臨江區(qū)域現(xiàn)設(shè)有安全圍擋,并立有岳陽市云溪區(qū)文管部門設(shè)置的文物安全公告公示欄。看著眼前這個不顯山不露水的銅鼓山,我突然生出一些疑問:3000多年前,當(dāng)時主要生活在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帶的商代人,為什么要跋山涉水來到相距遙遠的長江南岸?為什么來自北方的商人要以銅鼓山為聚居點?為什么商人來銅鼓山生活了400多年之后又會突然消失?……山脊間沉睡的青銅鼎與觚,或許正等待考古學(xué)家用聚落考古的鑰匙,解開商文化南遷的終極密碼。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我特意查閱了一些與之有關(guān)的歷史文獻。史學(xué)界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商人南下江南可能是為了掠奪長江中游地區(qū)較為豐富的銅礦、錫礦等與古代青銅器冶煉有關(guān)的資源。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他們積極將軍事勢力和商貿(mào)活動向長江以南拓展,銅鼓山遺址就是他們?yōu)楸U祥L江水運線路安全而建立的臨水戰(zhàn)略要塞,后來經(jīng)過多年建設(shè),才最終成為了商人南下的橋頭堡和中轉(zhuǎn)站。一些史學(xué)家甚至還認為,銅鼓山就是商代彭城的故址,因為先秦時期就有關(guān)于本地域是商代彭城的文字記載。岳陽市史志辦編纂的《岳陽歷代要事一覽》也明確記載:“2000多年前,建于大湘水與長江匯合處銅鼓山(今陸城境內(nèi))的大彭城,曾是商人南下的橋頭堡、中轉(zhuǎn)站。”從以上這些史料的記載和史學(xué)家的分析判斷基本可以確認:3000多年前,商人不顧路途遙遠南下江南,就是為了掠奪南方豐富的資源,特別是青銅冶煉原材料,因為青銅器當(dāng)時被商王朝視為“國之大器”,為了鑄造青銅器具,他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為什么從北方遠道而來的商人要將長江南岸的銅鼓山作為戰(zhàn)略要塞,并將其發(fā)展為橋頭堡、中轉(zhuǎn)站?我也在對有關(guān)史料文獻的梳理和實地的觀察思考中找到了一些答案。據(jù)史料記載,遠古時期的洞庭湖是非常廣闊的,要遠遠大于后代所說的“八百里”。并且,洞庭湖匯入長江的入口也不在今天的城陵磯附近。古時洞庭湖的湖口恰恰就在今天的陸城道仁磯至銅鼓山的這片水域,古時的湘江也是在此地與長江交匯的。這里臨江控湖,順江而下可達武漢地區(qū)的商代盤龍城,溯江而上則西抵荊州荊南寺、鄂西和川東地區(qū),向南則是湘江下游地區(qū),往東越過幕阜山的隘口可直達贛西北地區(qū)。
從地形地勢來看,冷兵器時代的銅鼓山確實是一個絕佳的戰(zhàn)略要塞。今天的地形地貌甚至還可看到昔日要塞的影子,銅鼓山矗立在長江南岸的沖積平原山,山勢不高,但四周視野開闊,有險可守。東面的馬鞍山是抵御長江南岸陸上侵擾的屏障,東面的長江大磯頭是控制下游水上舟船入侵的理想關(guān)隘。南面、西面是古代洞庭湖平原及洞庭湖與湘江、長江的交匯處,大江大湖阻隔,外來入侵者也難以隨意進出。北面的萬里長江更是銅鼓山天然的護城河。當(dāng)時的長江南岸還是蠻夷之地,除了部分土著原住民,很少有域外人光顧。但已開啟古代文明之光的商人,他們的智慧和眼界與南方土著民相比,早已不在同一維度,他們最終選擇將銅鼓山作為進入長江以南的要塞、橋頭堡和中轉(zhuǎn)站,就肯定考慮到了銅鼓山所具有的這些地理環(huán)境優(yōu)勢。
據(jù)專家考證,銅鼓山文化遺址早期相當(dāng)于中原商文化二里崗時盤龍城商文化類型,后期相當(dāng)于殷墟文化,屬土著文化遺存類型。從現(xiàn)有史料和考古發(fā)掘可以基本確認,銅鼓山商代文明一直延續(xù)到了東周時期,1987年銅鼓山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了大量東周墓葬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jù)。由此看來,銅鼓山商代文化存在有近400年的歷史。400年之后為什么會突然消失,現(xiàn)有的史料中還沒有找到任何片言只語的記載,也許是戰(zhàn)爭的屠城或洪災(zāi)等其他自然災(zāi)害的突然摧毀,我不敢妄加猜測。只能等待考古學(xué)家們未來對銅鼓山遺址的進一步發(fā)掘,也許可以從沉睡地下3000多年的歷史文物中,找到一些新的證據(jù)之后,才可破解這一謎團。
銅鼓山的歷史,如一部被歲月風(fēng)化的古老卷軸,其間的秘密或許比想象的更為深邃。我們這些匆匆過客,僅憑一游之時的淺見與臆測,又怎能輕易揭開它層層疊疊的神秘面紗?那些未解的謎團,如同山間繚繞的云霧,或許唯有歷經(jīng)時光的沉淀,由后世的智者與子孫們,以接力之姿,方能逐一撥開迷霧,讓真相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