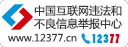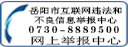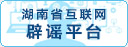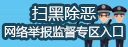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彭仁滿
在洞庭湖的浩渺煙波之東南,汨羅江水靜靜流到一座名曰“磊石”的古老山丘。世人皆知,此江因三閭大夫屈原懷沙殉國而名動千古。而磊石山腳下,正是屈原的靈魂歸去的地方。當我循著楚辭的幽徑,撥開歷史的云霧,一個更為深邃的秘密,如同江底的沉玉,漸漸顯露光華。
在屈原踏浪悲歌之前,這條汨羅江,早已被楚人的祖先奉為浩瀚星空的倒影,賦予了那個震爍千古的名字:“漢水”。漢水名在漢代后北移,成今天的江漢平原。這是顛覆我們當代認知的事情。
磊石為證 楚人的星河之江初名
磊石之名,質樸如山石壘疊。然而在楚人心中,它絕非凡丘。《禹貢》古卷中,它被尊崇為“東陵”(伏羲陵、夏王陵、楚王陵),是大禹丈量九州的神圣坐標(磊石禹書)。
遙想上古,先民們或許就站在這方高臺之上,仰觀蒼穹流轉,俯察大地脈絡。清代大儒胡渭,曾于青燈黃卷間窺得天機,他擲地有聲地斷言,《禹貢》所言“導漾東流為漢”之水,并非北方的漢江,正是這洞庭東去的汨羅清流!其根由,深植于楚人獨特的宇宙觀照。
想象那位傳說中的伏羲的身影——他曾立于磊石之巔八卦臺和觀星臺(考古已佐證)。他的目光,穿透漫長歲月,投向璀璨的星河。
那橫亙天際的光帶,楚人稱之為“云漢”或“天漢”。而當他的目光垂落人間,審視腳下這片澤國,汨羅江水系如銀練舒展,其流向竟與東南巽風(《易經》中象征“風”與“木”的卦位)暗合。
風行水上,木秀水湄——這是何等精妙的天地隱喻!
“漢水”——這從天而降的圣名,正是楚巫們在此的神圣空間,以星圖為經,以江河為緯,以《易》理為魂,為大地血脈進行的詩意加冕。
他們將銀河的無盡光輝,灌注于一條平凡的江水,使它成為溝通天人的液態圖騰。鄭玄慧眼獨具,道破玄機:“漢者,洞庭之野也……眾流縈回若云漢,故謂之漢。”一語道盡這天地輝映的壯闊詩篇。
文物與故地 “漢水”真身的千年佐證
時光的泥沙之下,歷史的真相從未湮滅。它們化身青銅的沉默、竹簡的墨痕,在千年之后發出驚雷般的回響。
在汨羅江上游的平江沃土,一尊青銅罍破土而出。它腹壁銘刻的“漢伯作寶尊彝”六字,如金石擲地。
這位西周早期的“漢伯”,統治著這片以“漢”為號的土地,他的宗廟必聞江聲湯湯。此器靜默宣告:早于屈原數百年,早于漢水之名北遷,“漢”的榮光已深深烙印在這條洞庭之濱的河流上。
與此同時,荊門包山楚墓冰冷的司法簡牘里有“羅之漢水有舟覆,溺三人”的公文記錄,不動聲色地揭示了一個事實——戰國楚人的官方文書里,汨羅江清晰無誤地被標注為“漢水”。冰冷的律法文字,竟成了溫暖鄉愁的佐證。
更撼動人心的,是源自清華簡《楚居》的古老歌謠。竹簡上墨跡如淚,吟唱著楚民族血脈的起源:“季連初降于隈山……抵于京宗(夏丘)。爰得妣隹……妣隹賓于天(難產而逝)……巫并該其脅以楚抵,曰‘漢水’,今曰汨羅。”
先祖季連之妃妣隹,在分娩的壯烈中回歸天界。悲痛的巫師以荊條包裹她的身軀,將她托付給奔流的江水,并以神圣的儀式為之命名——“漢水”。
《水經注》載:“汨水西流注湘,謂之漢潭。”《后漢書·郡國志》長沙郡載:“漢昌(平江),永壽元年(公元155年)置。”
“漢昌”為平江縣歷史曾用名,得名于境內昌水,后于唐代改稱“昌江縣”,五代時定名“平江縣”,其名稱演變始終與汨羅江(古稱羅水、汨水)的流域文化緊密關聯。據《平江縣志》記載,平江縣現存含“漢”字地名50處,如余坪鎮稻竹村的“漢水垅”,直接保留了“漢”字地名元素。周邊縣市亦分布密集:漢壽縣60處、汨羅市55處、湘陰縣39處、沅江市51處、岳陽縣47處、修水縣49處。其中,黃龍山作為汨羅江源頭之一,其周邊地名中“漢”字占比超17%。屈原管理區雖以“漢”字頭地名31處數量居后,但單位面積內占比顯著高于其他區域,凸顯其地名分布的獨特性。
這些流傳于今的“漢水”記憶,是見證洞庭北部磊石汨羅“漢水”名源的活化石。從此,這條江不再僅是地理的標識,它化作楚族創世神話的血脈,流淌著先祖的靈魂與民族的記憶。妣隹的“賓天”,便是“漢水”的“誕生”。這哪里是命名,分明是將一條河流,熔鑄成不朽的液態紀念碑!
名源之爭 被遮蔽的江南漢水正統
如此顯赫的“漢水”身世,為何竟被后世遺忘?一場延續千年的地理“名源戰爭”悄然上演。
自漢代孔安國等人起,許多經學家固執地將《禹貢》中的“嶓冢”指認為秦嶺山脈某峰,堅稱“漢水”即今日之漢江。
他們將“導”字強解為源頭,卻漠視了“嶓冢”不是山名,先秦指磊石山的伏羲、夏王、楚王三陵,最早來自屈原的《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是熊屈的盟約之所。難道他們要在敵國的土地上宣誓?顯然很荒誕。
“東陵”先秦是楚地的,與洞庭山、熊湘山、磊石山綁定成一個地理實體,必在洞庭。班固的筆輕輕一劃,竟將源頭北移陜西,磊石山周昭王、周穆王討伐先楚的“昭潭、穆屯”歷史真實地標,一下就變成了專家手中的傳說。
汨羅江的“漢水”身份,就這樣在中原中心論的正統敘述中被悄然遮蔽。
讓人深思的是,中原號稱華夏子孫,夏都的地理在中原尋找2000年無實處,又讓歷史變成傳說。有的學者還斷言中國文明史,只能從商代開始,6000年文明史就成了5000年。因為他們沒有正眼看待江南伏羲文明、夏文明活態傳承著的楚文明!
胡渭在《禹貢錐指》中,以地理學家的銳利目光,連發四矢,直指傳統謬誤,灉水之謎其描述的濕地景觀,唯有洞庭湖洲能完美契合;九江之辨“過九江”的地貌,非洞庭湖口九水匯流的磅礴氣象莫屬;東陵真身明確指出“東陵”即是洞庭巴陵山(先秦磊石山別稱);云夢坐標先秦云夢澤位于江南,更將“漢水”牢牢鎖定于洞庭水系。
現代巨擘周振鶴先生提出“地名隨移民遷徙”的理論,固然精妙,也是事實,但最早的源點在什么地方,當然要說清。但當考古的鋤頭叩響大地時,西周時期漢江流域青銅器上赫然刻著“沔”(如夨國尊銘“王在沔”)!
而汨羅江畔,“漢伯罍”卻以不容置疑的銘文宣稱:“漢”在這里!這并非遷徙的偶然,而是原地命名的光輝自證!地名遷徙之說,在“漢伯罍”的重器光芒前,顯得如此蒼白。
魂歸圣河 屈原與漢水的文明共鳴
當我們剝開歷史的層累,重現汨羅江——這條古老“漢水”的璀璨真身,再回望屈原行吟的江畔,便有了更深的悲愴與震撼。
《九章·哀郢》中痛呼:“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學者湯炳正洞悉幽微,指出“江夏”實指“江漢夏水”。屈原跋涉,所“遵”之“漢水”,正是腳下這條與他先祖血脈相連、被星辰祝福、承載創世神話的圣河——“汨羅漢水”!
公元前296年當他背對夏浦(今君山區),西望洪水淪陷的郢都,在“王棄沅湘”的悲憤中,哀“故都之日遠”。一語雙關,敘說的楚國的輝煌的先祖基業將消失的那無盡的哀思,不僅是對先祖故國的眷戀,更是沉入了一條流淌著楚魂源頭的生命之河。他戰死沉江于此,完成“獨立不遷”南國的最深沉、最壯烈的回歸與祭獻。融入了“將星空倒入大地”的創世時刻!
汨羅漢江就不再是一條普通的江,它是銀河落九天的投影,是楚魂不滅的詩篇,是中華文明多元根系中,一條被重新發現、流淌著星輝與史詩的“漢水”。
漢族、漢人、漢字、漢文將楚文化深度融合,它的名字,成了大地上永不褪色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