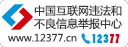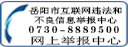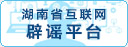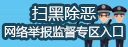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張步真
乙巳年九月十五日(2025年11月4日),是《岳陽樓記》誕生979周年,也是第三個“岳陽樓日”。這時,黃軍建同志的新作《滕子京:一個人與一座城》(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作家對一位曾經主政岳陽并做出了杰出貢獻的行政首長的由衷禮贊!
當我細細展讀這本書時,腦子突然跳出一個閃念:幸虧有個滕子京!
黃軍建以翔實的資料、精彩的敘說,描繪滕子京的博大情懷,意氣風發的實干家風采。他到岳州來的時候,不僅沒有耀眼的政治光環,反而戴著“罪臣”的帽子。然而,滕子京確信“縱然人生不會事事如意,但也沒有過不去的坎”。對他來說,“岳州無疑是他政治生命的一個新起點,是他重新煥發生命光彩的地方”。他沒有直接進岳州城,而是帶幾個幕僚,先去山村水鄉,實地調查、走訪。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岳州百業蕭條,百姓生活十分困難。這時,抓大事、抓主要矛盾,就體現一位官員的思想水平和執政能力。正式到職后,他立即端出一個菜單,即“五大會戰”:興商興業,建學宮,修南湖大橋,重修岳陽樓,筑偃虹堤。滕子京的眼光和謀略,不能不讓人由衷欽佩!
這部33.5萬字的皇皇大著,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滕子京的實干家精神。作為一位主政官員,滕子京實施他的工作計劃時,總是身先士卒,親臨第一線,沒有半點架子。比如,修南湖驛橋是一項民生工程,“滕子京坐鎮工場,組織石料,甄選能工巧匠”。在他的帶領下,“府衙三位監官把鋪蓋都搬到了工地上”,與工匠們同起落。而重修岳陽樓,知府大人更是親力親為,從籌集資金,到組織施工,每個環節他都在現場。一次,湖州大堤決口,沖擊樓基。滕子京一個北方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陣仗,他不敢有些微僥幸,通宵達旦地守在大堤,指揮搶險,最后“倒在了工地上,被衙役抬回府衙”。一位州府一級的官員,如此不計個人安危,沖鋒在前,這在封建王朝絕對是鳳毛麟角的。
當然,滕子京的這些特點,以前主政過岳州的官員也可能具備。黃軍建作為故事的講述者,精彩地描繪了滕子京在岳州的神來之筆,那就是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
重修岳陽樓的工程進行得十分順利。這時,滕子京心心念念想的是要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我們可以做一點假設:假如滕太守沒有文化素養,不懂得“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滕子京《致范仲淹〈求記信〉》)。假如滕子京跟范仲淹素不相識,或者兩人不是同時考中進士的“年兄”;也或者兩人雖然是老同學,卻政見相左,話不投機半句多;更或者他們是那種“當面握手言歡,背后使絆子”的官場冤家死對頭……凡此種種,都不會有這篇光照千秋的《岳陽樓記》!中華文化寶庫里就將少了“先憂后樂”這塊瑰寶,岳陽的文化名城地位也將大大降格。時過境遷之后,遙想當年,心里頭都覺得十分后怕!
讀黃軍建的新著,還發現他的文筆日臻成熟,既老練又靈動,同時還攝入了現代元素。比如,他寫洞庭湖的落日:“從橘紅走向粉紅,滑向淡黃、隱向灰黃,最終隱去。”他寫“滕子京的腦袋就像一臺超級電子計算機,總在不停地以每秒百萬次躍動,為岳州的塑形、修飾、點綴,絞盡腦汁……”這完全是現代語言。我認為這也是必須的。屈原的《離騷》中,有許多上古時代的人物與故事,他的文筆卻是汲取了彼時楚地的民歌形式。杜甫寫《登岳陽樓》,是用唐代的語言。因為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會有特定的語言模式和心靈圖譜。寫歷史人物,注入現代元素,更有利于當代讀者的閱讀和親近。當然這需要出神入化。
黃軍建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也值得稱道。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聚焦于岳陽樓、范仲淹和滕子京。他既做田野調查,又在故紙堆里尋覓,合理借鑒別人的學術成果。一輩子專注于一件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執著,以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決心,成就了1500萬言的著述,全面闡述了岳陽樓及范、滕二公光彩照人的風采。為“憂樂精神”的光大立下了功勞,為文化名城壯了聲威,同時也為“岳陽樓學”成為一門“顯學”做出自己的努力。這種癡情,使他本人成為“范學”“樓學”方面的專家。
岳陽自晉武帝(公元266—290年)時期單獨開埠建制,1740多年來,以平均每3年1個任期,先后主政過岳州的官員大約580余位。這些官員在任時,大都聚精會神謀發展,為岳陽的繁榮昌盛做出了貢獻。更值得慶幸的是,慶歷年間岳州來了個滕子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