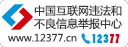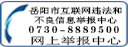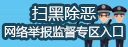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 陳籽欣
范仲淹筆下的洞庭湖,是“朝暉夕陰,氣象萬(wàn)千”,這短短幾字的重量不容小覷,壓得住八百里云夢(mèng)澤。而南湖,是這萬(wàn)千氣象中,如女媧補(bǔ)天遺落的一塊仙石,看盡了世間煙火。
鳥(niǎo)雀呼晴,南湖于侵曉時(shí)分被喚醒。朝陽(yáng)正忙著織造金燦燦的云錦,一切的氤氳霧氣皆被拭凈,水光山色,悉在鏡中。此時(shí)的空氣還未從那場(chǎng)清冷遙遠(yuǎn)的舊夢(mèng)中蘇醒,涼潤(rùn)透明,流水一般地淌過(guò)萬(wàn)物,又是那么薄薄一層,用剪刀輕輕一裁就裁開(kāi)了。流光在湖面上微微浮漾,碎金一湖,溢彩千頃。水聲潺潺,與清脆的鳥(niǎo)鳴共奏一曲晨間美樂(lè)。
南湖開(kāi)始熱鬧起來(lái)了:騎行的年輕人時(shí)不時(shí)經(jīng)過(guò);環(huán)湖散步的不忘外放著早間新聞;偌大的空地上,聚著一群打太極的老人。錄音機(jī)的樂(lè)聲裹著電流的微噪,仿佛隔著一層水傳來(lái)。他們的神情逐漸平和,是一種將紛擾世事關(guān)在心門之外的靜穆,此刻的吐納仿佛正與山川湖水對(duì)話。最前一位白衣老人的雙手正推著一團(tuán)無(wú)形的氣,雖看不見(jiàn)摸不著,卻仿佛能感受其溫度與韌勁。起手,靜若掬水;云手,如攬流云。連衣角都在風(fēng)中有規(guī)律地顫動(dòng),一招一式,動(dòng)作如湖水般,充滿內(nèi)在的韻律。南湖,孕育了一天的新生。
午后的南湖,風(fēng)和日暖。藍(lán)穹飽滿,像敲上去能敲出輕音樂(lè)的巨大水晶,湖水悠悠蕩蕩,攪皺樹(shù)影與云。這時(shí)的湖面不是一整片明晃晃地亮,而是細(xì)膩的、溫柔的,像塊上好的綢緞,但風(fēng)一過(guò),又被揉成了千萬(wàn)粒碎銀子,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仨憽C鞔膶W(xué)家袁宏道稱贊西湖“花光如頰,溫風(fēng)如酒,波紋如綾”,我想,南湖也并不遜于此。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攝影的老先生。他常于午后來(lái)到三眼橋附近,將鏡頭長(zhǎng)久地、沉默地對(duì)著三眼橋,似乎在等待一朵宋代的云,重新從橋洞中飄出。老先生按下快門的動(dòng)作很利落,仿佛要通過(guò)定格的照片,捕捉一段曾經(jīng)。或許他也有過(guò)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懷,亦懂得杜甫“老病有孤舟”的蒼涼。如今,南湖又靜靜映照著他的晚年。舊故里草木深,石縫里擠出的青苔厚重得像塊綠絲絨,這座三眼橋始建于慶歷年間,千百年來(lái),無(wú)數(shù)雙足跡在上面走過(guò),一座橋上有多少故事,一湖水中就藏著多少悲歡。
最先感受到時(shí)間流逝的,是湖水的顏色。夕照是把經(jīng)久不息的野火,那片蔚藍(lán)從西邊被悄悄點(diǎn)燃,一直燒出橙紅的、玫瑰金的光暈。一湖的琥珀融化,流淌。晚風(fēng)帶來(lái)溫潤(rùn)的水汽,如母親的雙手撫去這塊土地上的所有疲憊。湖南理工學(xué)院內(nèi)有座音樂(lè)臺(tái),正面對(duì)著南湖。傍晚時(shí)分,便有人演唱。那歌聲在晚風(fēng)與湖水里晃漾,倒像是從一臺(tái)老收音機(jī)里傳來(lái)的,溫暖、繾綣、有種不真切的懷舊感。石階上坐著的,有彼此依偎的戀人,有談天說(shuō)地的好友,有靜默不語(yǔ)的老人,有嬉笑玩鬧的孩童……眾生萬(wàn)象,都在這歌聲中化作南湖記憶的一脈水波。
暮色終于濃成黑夜。月像一枚冰制的印章,蓋在幽藍(lán)的天幕上,明河共影,一湖清輝。獨(dú)坐南湖邊,能聽(tīng)見(jiàn)湖水呼吸的聲音,那是一種低沉的、來(lái)自大地深處的脈搏。天地悠悠,湖中月亦是天上月,張若虛那句“江畔何人初見(jiàn)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便不由自主地浮上心頭。此刻的南湖,不就是千年前的那條春江嗎?
江水流春去欲盡,古人的生命早已隨著南湖的水流入歷史,但今朝的一次仰頭,我看見(jiàn)了千年前的一輪月,聽(tīng)到了千年前湖水潺潺之聲。當(dāng)凝望月亮?xí)r的那份孤獨(dú)、那份對(duì)美的震顫、那份對(duì)命運(yùn)的叩問(wèn),通過(guò)這同一片月光,飄落在我的心上時(shí),我知道,南湖的月,月的南湖,再次等來(lái)了它所等待的人。
身旁的手機(jī)振動(dòng),是家人發(fā)來(lái)關(guān)懷的信息,一種奇異的幸福涌上心頭。千年明月依舊,今夜,我獨(dú)享著一湖月色,以及一份對(duì)生命的期待與被期待。
轉(zhuǎn)身離去,南湖依舊,明月依舊。等待下一個(gè)月落日升,新一輪的南湖時(shí)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