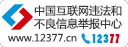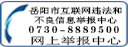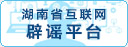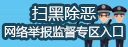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李晗妮
深秋的午后,陽(yáng)光透過(guò)窗欞,在湖南理工學(xué)院美術(shù)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劉文良的工作室里投下斑駁的光影。屋內(nèi)陳列著湘西木雕、宋代瓷片,每一件器物都靜默地訴說(shuō)著時(shí)光的故事。這里不像傳統(tǒng)的收藏室,倒像是一方心靈棲息之地,處處流露著主人對(duì)生活的思考與熱愛(ài)。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木香和舊物的氣息,仿佛時(shí)間在這里放緩了腳步,讓人不由自主地靜下心來(lái)。
“我從來(lái)不在乎它們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劉文良摩挲著一片未清洗的宋代瓷片,“這些物件是我與精神對(duì)話的窗口,是自己營(yíng)造的一個(gè)安靜之處。”在他的眼中,收藏不是資本的追逐,而是精神的回歸;不是對(duì)物質(zhì)的占有,而是對(duì)文化的守護(hù)。這些被世人視為“破爛”的東西,在他這里卻是無(wú)價(jià)之寶,因?yàn)樗鼈冞B接了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物質(zhì)與精神,個(gè)體與文明。
退后一步 收藏中的人生智慧
在這個(gè)人人向前狂奔的時(shí)代,劉文良提出了一個(gè)發(fā)人深省的問(wèn)題:“大家都在往前沖的時(shí)候,是不是還有一種方式是退后的?”
他的收藏實(shí)踐,正是對(duì)這種“退后哲學(xué)”的生動(dòng)詮釋。不同于那些追逐拍賣(mài)會(huì)、關(guān)注市場(chǎng)價(jià)值的傳統(tǒng)藏家,劉文良更鐘情于在洞庭湖邊撿拾瓷片,在湘西村落尋訪木雕。這些行為看似“退后”,卻讓他獲得了更深層的前進(jìn)力量——與歷史對(duì)話的能力。他常常一個(gè)人走在湖邊,低頭尋找被湖水沖刷上岸的瓷片,他認(rèn)為每一片都可能來(lái)自唐宋,甚至更早。這個(gè)過(guò)程,在他看來(lái),是一種冥想,也是一種修行。
“無(wú)用之用,方為大用。”劉文良指著墻上掛著的湘西木雕說(shuō)道,“這些在別人眼中無(wú)用的東西,卻匯聚成生活的各種可能。”他在南湖畔后浪公園展示學(xué)生的畫(huà)作和自己收藏的木雕,他經(jīng)常對(duì)學(xué)生說(shuō):“不是要教導(dǎo)人們?nèi)绾舞b賞藝術(shù),而是希望啟發(fā)大家思考: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當(dāng)下,那些看似無(wú)用的時(shí)間投入、情感傾注,或許正是滋養(yǎng)心靈的沃土。”他組織的工作坊和展覽,從不標(biāo)價(jià),也不拍賣(mài),只是靜靜地呈現(xiàn),讓觀者自行感受器物背后的溫度與故事。
這種“退后”的智慧,何嘗不是對(duì)現(xiàn)代生活的一種矯正?當(dāng)效率至上成為社會(huì)運(yùn)行的邏輯,當(dāng)價(jià)值衡量一切成為思維定式,劉文良的收藏實(shí)踐提醒我們:生活還有另一種可能——慢下來(lái),退一步,或許能看得更清楚。他說(shuō),收藏教會(huì)他的不是擁有,而是放下;不是前進(jìn),而是回望。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他找到了內(nèi)心的平靜與自由。
AI時(shí)代的啟示收藏中不可復(fù)制的人性光輝
面對(duì)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劉文良有著獨(dú)特的思考:“AI可以復(fù)制很多東西,但復(fù)制不了思想、情感和敬畏之心。”
在他的收藏中,每一件物品都承載著工匠的心血與情感。湘西木雕的野性奔放,宋代瓷片的滄桑古樸,都不是機(jī)器能夠批量生產(chǎn)的。“民間藝術(shù)的精華,融入了工匠一輩子的心血和對(duì)事情認(rèn)真對(duì)待的態(tài)度。”劉文良說(shuō),“這里面包含著人性的美,包含著真善美的釋放。”他拿起一件湘西儺面,解釋道:每一個(gè)線條、每一刀雕刻,都是匠人情感的流露,是對(duì)自然的敬畏,對(duì)生活的理解。這是機(jī)器無(wú)法模擬的,也是AI難以替代的。
當(dāng)今社會(huì),技術(shù)能夠模仿風(fēng)格、復(fù)制形式,甚至創(chuàng)造看似新穎的作品,但卻很難真正擁有那種“從土壤里生長(zhǎng)出來(lái)的自由天性”。劉文良認(rèn)為,真正的創(chuàng)新不是實(shí)驗(yàn)室里冥思苦想出來(lái)的,而是從生活的土壤中自然生長(zhǎng)出來(lái)的。他舉例說(shuō),湘西的刺繡、苗銀、土布,都是當(dāng)?shù)厝嗽陂L(zhǎng)期的生活實(shí)踐中逐漸形成的,它們與土地、氣候、民俗緊密相連,是文化的活態(tài)傳承。
對(duì)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一思考尤為珍貴。“AI可以幫你完成很多普遍性的工作,但天性是機(jī)器替代不了的。”劉文良在教學(xué)中注重引導(dǎo)學(xué)生從民間藝術(shù)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培養(yǎng)他們的歷史文化素養(yǎng)和情感融入能力——這些正是AI難以復(fù)制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他常常帶學(xué)生下鄉(xiāng)采風(fēng),接觸民間藝人,感受最原生態(tài)的藝術(shù)形式。他說(shuō),教育的本質(zhì)不是灌輸知識(shí),而是喚醒天性,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收藏藝術(shù)提醒我們:在技術(shù)日新月異的時(shí)代,那些最古老的人類特質(zhì)——情感、敬畏、匠心,或許才是最值得珍視和培養(yǎng)的寶貴財(cái)富。劉文良說(shuō):“我們不能因?yàn)榧夹g(shù)的進(jìn)步而忽視了人性的根本,我們應(yīng)該更加重視那些機(jī)器無(wú)法取代的東西。”
文化根脈 收藏中的精神歸宿
劉文良的收藏有一個(gè)特點(diǎn):絕大多數(shù)物品都來(lái)自湘西地區(qū)和他生活的岳陽(yáng)。“我不想獵奇,只收集自己真正了解和文化上有連接的東西。”他說(shuō)。
這種選擇背后,是一種文化自覺(jué)和自信。在他看來(lái),沈從文的文字、黃永玉的畫(huà)作、宋祖英的歌聲,都是從湘西土壤中生長(zhǎng)出來(lái)的文化果實(shí)。“為什么湘西能出這么多文化名人?因?yàn)槟抢锏奈幕寥莱缟刑煨葬尫牛谎?guī)蹈矩。”他進(jìn)一步解釋道,湘西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山水環(huán)境的獨(dú)特性,造就了這里文化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每一種藝術(shù)形式,無(wú)論是舞蹈、音樂(lè)還是工藝,都帶有強(qiáng)烈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氣息。
劉文良談到湘西的“趕尸”習(xí)俗,他認(rèn)為這其實(shí)源于湘西人“死在外面一定要回到自己土地”的念想。他認(rèn)為,每一種文化現(xiàn)象都有其淵源,都是一脈相承的。他的收藏,就是對(duì)這種文化脈絡(luò)的梳理和保存。他不僅收藏器物,還記錄背后的故事和習(xí)俗,試圖構(gòu)建一個(gè)完整的文化圖景。他說(shuō),收藏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理解,為了傳承。
在全球化浪潮中,這種對(duì)本土文化的堅(jiān)守別具意義。劉文良說(shuō):“我們必須從民間藝術(shù)、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出路。這不僅是對(duì)文化的傳承,更是對(duì)自我身份的確認(rèn)。只有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才能生長(zhǎng)出真正有生命力的藝術(shù)花朵。”他呼吁年輕人多關(guān)注本土文化,不要盲目追逐外來(lái)潮流,而是要從自己的根脈中尋找靈感和力量。
對(duì)于當(dāng)代人而言,這種文化根脈的追尋更顯迫切。在物質(zhì)豐富卻精神貧瘠的今天,收藏成為一種尋找精神歸宿的方式——通過(guò)物與歷史的連接,找到自己在文化長(zhǎng)河中的位置。劉文良說(shuō):“每一件藏品都是一個(gè)坐標(biāo),標(biāo)記著文化的流變與延續(xù)。”
回歸生活 收藏的終極意義
采訪結(jié)束時(shí),劉文良拿起一塊隨性在路邊撿到的石頭:“你看,這個(gè)石頭就像民國(guó)大家款款向我走來(lái),穿著白袍。與之初見(jiàn)的那種感覺(jué),是一瞬間的感動(dòng)。”
這句話道出了收藏的真正意義——不是投資增值,不是附庸風(fēng)雅,而是在平凡生活中發(fā)現(xiàn)不平凡的美,在物質(zhì)世界中尋求精神的共鳴。他說(shuō),收藏的最高境界是“物我兩忘”,是通過(guò)器物達(dá)到與歷史、文化和自我的對(duì)話。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人變得謙卑,也變得豐富。
劉文良的收藏哲學(xué),最終指向的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做人應(yīng)該“往無(wú)聲處藏”,做藝術(shù)則要“往規(guī)矩外跑”。這種態(tài)度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心的寧?kù)o與自由的天性,從各種人設(shè)和框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他說(shuō),現(xiàn)代人太在意外界的評(píng)價(jià)和物質(zhì)的積累,反而忽略了內(nèi)心的聲音和真正的需求。收藏,于他而言,是一種反叛,也是一種回歸。
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這種生活態(tài)度顯得尤為珍貴。當(dāng)外賣(mài)取代了廚房的煙火氣,當(dāng)手機(jī)交流取代了面對(duì)面的真情實(shí)感,當(dāng)結(jié)果導(dǎo)向取代了過(guò)程體驗(yàn),劉文良的收藏實(shí)踐提醒我們:生活不應(yīng)該被簡(jiǎn)化為目的性的追逐,而應(yīng)該是豐富的體驗(yàn)和感受。他說(shuō),人生的意義不在于擁有多少,而在于體驗(yàn)多少,感受多深。
“人的一輩子不是奔向死亡,而是體驗(yàn)感受。”收藏室內(nèi),每一件物品都是這種體驗(yàn)的見(jiàn)證,都是生活哲學(xué)的具象表達(dá),是生命的一部分。
走出劉文良的工作室,夕陽(yáng)西下。回首望去,他的收藏空間在余暉中顯得格外溫暖。或許,真正的收藏不在于藏品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而在于它們所能喚起的情感共鳴和文化思考;不在于占有多少器物,而在于通過(guò)這些器物與多少故事、多少歷史、多少人文精神相連接。
在AI 技術(shù)日新月異的今天,在文化融合與沖突并存的時(shí)代,劉文良的收藏實(shí)踐給我們以啟示:無(wú)論技術(shù)如何進(jìn)步,那些最人性化的特質(zhì)——情感、敬畏、匠心,永遠(yuǎn)是最寶貴的財(cái)富;無(wú)論世界如何變化,扎根自己的文化土壤,永遠(yuǎn)是創(chuàng)新與自信的源泉。
藏物,更是藏心、藏道。這或許就是收藏藝術(shù)給予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最珍貴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