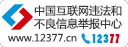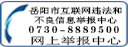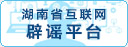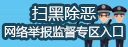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平江縣第六中學 胡瑤
又是一年中秋至,桂香浮動,月華如練。可自2021年起,這片象征圓滿的銀輝,便為家中的節日,蒙上了一層難以言說的清寂。
清晨,我帶著兒女回到娘家。孩子們雀躍著撲進外婆懷里,我則獨自靜靜上樓,在父親的遺像前駐足。指尖輕撫過相框里那熟悉的容顏,淚水瞬間模糊了視線——那個曾用脊背為我撐起整片天空的人,再也無法在月圓之夜,與我相見了。
父親生于寒門,身為長子,十六歲便用稚嫩的肩膀,一頭挑起了生活的重擔。記憶里,他的身影總與黎明前的黑暗融為一體。他騎著一輛舊自行車,后座上的貨物堆得比頭還高,用彩色的粗麻繩緊緊捆縛,像一座移動的小山。“嘎吱嘎吱”的鏈條聲,碾過凌晨五點的寂靜,成了我童年記憶里最熟悉的韻律。那時我不懂,為何他總在午間歸來時,能變戲法般地從口袋里掏出外面買來的糖果;后來才明白,那是他天不亮就出發、往返奔波兩趟后,專門繞路為女兒帶回的甜蜜。
十八歲那年的盛夏,望著他被歲月壓彎的脊背,我忍不住追問:“爸,不能少跑一趟嗎?”他停下手中的活,用粗糙的手掌輕撫我的發頂,笑容里藏著說不盡的疲憊:“一大家子都要吃飯啊。”
后來,自行車換成了摩托車,摩托車又換成了三輪車。生活的擔子仿佛輕了些,可奔波中的風險,卻從未遠離。直到多年后,我才從母親無意的話語中得知,高二那年,他清晨經過家門口那座窄橋時,連人帶車翻入橋底。萬幸,蒼天垂憐,未造成大礙。而這驚心動魄的一幕,被他以一句“沒事”輕輕帶過,默默藏在了心底。
在我的記憶里,家里的中秋總是來得格外早。父親是做月餅的好手,餅皮上總有他拇指壓出的獨特印記,餡料里的冬瓜糖總比別人家多切一分。那些各式各樣的印模,每年只有在他手中,才能壓出最勻稱、最精美的圖案。每年暑假,月餅的甜香便彌漫了整個院落,十余名工人在他的指揮下忙碌,他卻始終將我隔絕在煙火之外,話語樸素而堅定:“你是讀書的料。”
于是,妹妹在作坊里穿梭,我在書房中苦讀。許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那方小小的書房,是他耗盡心力為我筑起的象牙塔。雖然后來我未能金榜題名,他卻從未有過半句責備,只是摸了摸我的頭說“沒事,盡力就好”,轉頭又將希望的火種悄然傳遞給了妹妹。這份沉默的包容,成了我心底一份永遠溫柔的虧欠。
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總想著待我羽翼豐滿,能好好反哺他時,再讓他安享晚年。奈何命運在最猝不及防時露出獠牙——2014年夏天,四十五歲的父親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醫生宣判的五年期限,如同晴天霹靂,將我剛剛展開的人生,驟然攪亂。
手術后,他執意將畢生積蓄塞到我手里:“別浪費錢了。”母親在一旁紅著眼眶堅持:“這是你的血汗錢,必須用在你自己身上。”自此,我們母女三人攜起手來,續寫這場與死神的漫長拉鋸。七年,住院單累積到第六十三次,所有能試的靶向藥都試了個遍。
腫瘤科主任后來曾動容地對我說:“你父親是我見過最堅強的病人。也正是你們母女三人無微不至的愛,給了他抗衡命運的驚人意志。”是啊,我們原本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子。這份雙向的愛,便是我們共同對抗病魔的鎧甲。
在病魔面前,他始終保持著不可思議的從容,甚至強撐病體,親自操辦完我們姐妹的婚事,見證了孫輩的降臨。為了減輕我的負擔,他和母親又執意幫我撫養兒子——如今,兒子的眉眼神情、秉性脾氣里,處處都是他外公的影子。
直到我分娩女兒,正在月子里時,他終究如風中燭火,在2021年5月23日,靜靜地熄滅了。三十載父女緣分,到此戛然而止。有人說,一個父親愛女兒最好的方式,是在她能看淡生死的年紀離開。可我年屆三十,又如何能看淡這生死之別?
他傾其一生,予我山海般的深情,我卻再無緣回報分毫。“子欲養而親不待”,這七個字,從此在我生命里有了刻骨的重量與形狀。
如今,每至中秋,當銀輝再度灑滿庭院,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那是在苦難中淬煉出的堅韌,在貧寒里堅守的善良,是在命運重壓下依然挺直的脊梁,更是對父母盡孝、為兄妹擔當的無盡責任。
父親雖已化作了天上月,卻永遠是我在人間路上,最亮、最溫暖的那座燈塔。每逢月圓,那灑下的清輝便如他的牽掛,溫柔地灑滿我前行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