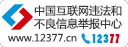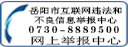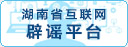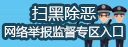平江縣獻(xiàn)鐘小學(xué) 余仁保
這幾日,接連三位母親的囑托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上。那未曾帶回家的課本、那總是“做了做了”的含糊其辭、那手機(jī)屏幕后躲閃的眼神,連同母親們焦灼的嘆息,仿佛勾勒出一幅共同的圖景:教育的重心,正失衡地、幾乎全部地,向著學(xué)校這一方傾斜。這讓我想起尹建莉老師在《好媽媽勝過(guò)好老師》中那句沉靜而有力的話:“家長(zhǎng)和老師,不是誰(shuí)交給誰(shuí)一個(gè)孩子,而是共同守望他的成長(zhǎng)。”這份“共同”的責(zé)任感,在當(dāng)下似乎正變得稀薄。
那位將孩子的學(xué)業(yè)“全靠老師了”的母親,其無(wú)奈背后,是家庭教育力量的某種退卻。我絕非指責(zé),我深知生活的重壓與教育的復(fù)雜。但正如孫云曉先生在《教育的根本》里所洞見(jiàn)的:“教育的根在家庭,教育的干在學(xué)校,教育的果在社會(huì)。”若根須未能深扎于溫暖而堅(jiān)定的土壤,僅憑學(xué)校這“干”如何能獨(dú)自支撐起一棵參天大樹(shù)?那個(gè)總說(shuō)作業(yè)“做了做了”的聰明男孩,他缺失的或許并非智力,而是一種在家庭環(huán)境中被悄然培養(yǎng)的習(xí)慣與品格。孫云曉先生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習(xí)慣的養(yǎng)成如同紡紗,每一天的重復(fù)都至關(guān)重要,而最初的那根線,無(wú)疑掌握在父母手中。
這并非意味著父母需成為無(wú)所不能的“家教”。恰恰相反,尹建莉老師提倡的是一種“有質(zhì)量的陪伴”。它不在于時(shí)刻緊盯作業(yè)本,而在于營(yíng)造一個(gè)書(shū)香彌漫的客廳,一次飯后關(guān)于趣聞的閑聊,一份面對(duì)挫折時(shí)的鼓勵(lì)與信任。那個(gè)周末不帶書(shū)回家的女孩,她所需要的“抓緊”,或許并非我在課堂上的額外督促,而是母親在周末清晨,伴她一同翻開(kāi)書(shū)本的半小時(shí)寧?kù)o時(shí)光。這種氛圍的熏陶,遠(yuǎn)勝于任何外在的強(qiáng)制。它是一種“潤(rùn)物細(xì)無(wú)聲”的滋養(yǎng),是《好媽媽勝過(guò)好老師》中格外看重的“潛教育”力量。
而作為教師,我的角色又當(dāng)如何?朱永新教授在《教育的細(xì)節(jié)》中給了我啟示:“教育的光芒,往往閃爍于那些被成人世界所忽視的細(xì)微之處。”當(dāng)我面對(duì)那個(gè)沉迷手機(jī)的孩子,除卻“在學(xué)校多強(qiáng)調(diào)”,我更應(yīng)去探尋他指尖滑動(dòng)的世界里,究竟有什么比現(xiàn)實(shí)更吸引他?是缺乏更有趣的活動(dòng),還是渴望逃避某種壓力?教育,需要這樣一份洞察細(xì)節(jié)的耐心與慈悲。雖然我不能替代家庭的功能,但我可以嘗試成為連接家校的橋梁,用專業(yè)的知識(shí)與持續(xù)二十五年的觀察,去理解每一個(gè)行為背后的“為什么”,并嘗試與父母?jìng)兎窒磉@種觀察。
我深知,要求所有父母都成為教育專家,是奢侈且不現(xiàn)實(shí)的。但教育的核心,從來(lái)不是知識(shí)的單向灌輸,而是生命對(duì)生命的深刻影響。正如《好媽媽勝過(guò)好老師》中所言:“父母對(duì)待孩子的方式,正是孩子未來(lái)對(duì)待世界的方式。”我們期待孩子誠(chéng)實(shí),那么我們是否給予了他不必撒謊的寬容環(huán)境?我們期待孩子勤奮,那么我們是否讓他看到了我們?yōu)樯钆Φ哪樱?/p>
歸根結(jié)底,教育是一場(chǎng)優(yōu)雅而需要默契的“雙人舞”。家庭與學(xué)校,如同兩位舞伴,一進(jìn)一退,一牽一放,都需要把握恰到好處的節(jié)奏與力量。父母那充滿關(guān)愛(ài)與規(guī)則的“牽手”,給予孩子最初的安全感與方向感;而適時(shí)的“放手”,則考驗(yàn)著教師的智慧與胸懷,讓孩子在更廣闊的空間里探索自我。
鈴聲又將響起,我將走進(jìn)教室,面對(duì)那一張張純凈而復(fù)雜的臉龐。我無(wú)法將教育的全部重?fù)?dān)攬于己身,但我愿以這二十五年積攢的耐心與思考,更主動(dòng)地走向舞伴——那些或焦慮、或無(wú)奈的父母?jìng)儭W屛覀円煌毩?xí)這支“雙人舞”吧,不是為了完美無(wú)缺的表演,而是為了我們共同守望的那個(gè)成長(zhǎng)中的生命,能最終找到屬于自己的、自由而穩(wěn)健的舞步。